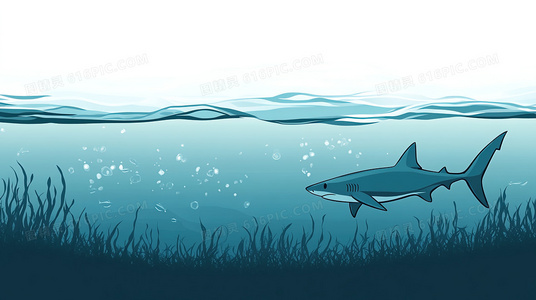六月的蝉鸣,是撕开记忆的第一道口子。

它们藏在老槐树油亮的叶子后面,藏在教学楼斑驳的影子里,藏在操场尽头那排锈蚀的单杠之间。那声音不是唱,是锯,用生锈的钢锯条,一下一下,锯着午后的神经,锯着时间的骨头。三年前的六月,也是这样的蝉鸣,也是这样能把柏油路面晒出油来的太阳。父亲就是在这样的蝉鸣声里倒下的,倒在建筑工地十七楼的未完工的框架边缘,像一片突然被风卷走的枯叶。没有遗言,只有安全帽滚落时,在水泥地上敲出空洞的回响,一下,又一下,混进了铺天盖地的蝉声里。
拳头,就是从那时握紧的。
他记得自己怎样冲进那间弥漫着劣质烟草和汗味儿的项目经理办公室,记得那个矮胖男人油光发亮的额头,和不断开合的、金牙闪烁的嘴。话语像泥鳅一样滑溜:“意外,纯属意外……流程……保险……公司有规定……”每一个词都轻飘飘的,试图抹去一个生命的重量,抹去一个家庭的支柱。父亲的工友,那些黝黑、皱纹里嵌满水泥灰的男人们,围在一旁,嘴唇嗫嚅着,眼神躲闪着,他们的手也曾握紧,又无奈地松开,最后只是沉重地拍了拍他单薄的肩膀。那一刻,十七岁的少年,把所有的愤怒、无措、崩塌的世界,都压缩进了右手紧握的拳头里。骨节捏得发白,指甲深深陷进掌心,留下四个月牙形的血痕,很久都没有消退。
此后的日子,拳头成了他身体的一部分,一种沉默的姿势。上课时握着笔,拳头是僵硬的;骑车穿过繁华的街市,拳头抵在车把上;夜里躺在吱呀作响的木板床上,拳头抵着冰凉的墙壁。它里面包裹着一团火,一团名为“不公”的毒火,炙烤着他的心肺,也支撑着他不要倒下。他变得沉默,锋利,像一把未出鞘却时刻绷紧的刀。他疯狂地学习,因为有人说过,知识是力量。他要这力量。他避开人群,因为怜悯的目光让他拳头发痒。母亲在一夜之间枯萎下去,又迅速地被生活催逼着,去餐馆洗碗,去楼道做保洁,腰身佝偻下去,沉默得像一块礁石。他们之间的话越来越少,偶尔的目光相接,都迅速弹开,怕触碰到彼此眼里那片深不见底的、雷同的废墟。家,成了一个安静地陈列着伤痛的空壳,只有他紧握的拳头,是里面唯一还在躁动、还在抗议的活物。
改变是细微的,像墙角渗出的水渍,慢慢洇开。
先是母亲。某个他熬夜刷题的凌晨,母亲轻轻推门进来,放下一碗撒了葱花的素面,手指无意间拂过他紧握在课本旁的拳头。那手指粗糙,温热,带着洗洁精和漂白水混杂的、并不好闻的气息,却像一根突然探进冻土的春芽,让他悚然一惊。母亲什么也没说,只是停留了那么一瞬,便掩门离去。他看着那碗面上升起的、纤细而执拗的热气,第一次感到拳头里的火,烧得有些虚空,有些疲惫。
然后是那些“他们”。那个总在巷口修车、少了一根手指的李伯,硬塞给他两个茶叶蛋,“小子,脸色不好,补补。”那个父亲曾经的工友老陈,在菜市场撞见他,远远喊了一声,追上来,往他菜篮子里塞了一把嫩青菜,嘟囔着“自家种的,吃不完”,便转身匆匆走了,背影有些仓皇,却不再是最初那种纯粹的躲闪。甚至,那个曾让他恨得牙痒的、父亲工地上的小包工头,在一次街头偶遇时,竟也脚步迟疑了一下,脸上掠过一丝极复杂的、难以形容的愧怍,虽然最终仍是低头快步离开。这些细碎的、不成逻辑的暖意,像一点点微弱的雨滴,落在他心田那龟裂的、愤怒的硬壳上,起初毫无痕迹,却不知何时,开始了缓慢的渗透。
真正的“看见”,发生在一个同样闷热的午后。他去母亲工作的那栋写字楼送钥匙。在消防通道的角落里,他看见母亲。她正费力地擦拭着高大的玻璃窗,踮着脚,伸长手臂,身体绷成一张吃力的弓。午后的阳光穿透玻璃,毫无保留地倾泻在她身上,照亮了她鬓角刺眼的白发,照亮了她额头上密集的汗珠,也照亮了她沉静的、甚至近乎麻木的侧脸。那脸上没有怨恨,没有控诉,只有一种巨大的、吞咽下一切的疲惫,和一种更巨大的、从这疲惫深处生长出来的、近乎笨拙的坚持。就在那一刻,窗外的蝉鸣前所未有地尖锐起来,像无数把锉刀,同时锉着他的耳膜,锉着他的心脏。他忽然听懂了那噪音——那并非示威,也非欢唱,而是生命在极度闷热与挤压中,本能发出的、粗粝的呼吸。每一个鸣叫的蝉,都曾在地下蛰伏漫长的黑暗岁月。它们钻出地面,爬上枝头,挣破外壳,用尽全部力气嘶鸣,不过是为了完成一个季节的、短暂的传承。然后,在秋风中寂然死去。
母亲,父亲,李伯,老陈,甚至那个包工头……他们何尝不是如此?在生活的十七楼边缘,在各自的“地下”,沉默地承担,挣扎,呼吸,最终完成或未完成他们的“嘶鸣”。愤怒的拳头,能打破这循环吗?握紧的拳头,能接住母亲额角的汗,能填平父亲坠落后留下的深渊吗?
蝉声如浪,一阵高过一阵,达到顶峰,然后在某个瞬间,仿佛被太阳晒化了似的,呈现出一种奇异的、透明的平静。
他慢慢地,松开了右手。
指关节发出生涩的、轻微的“咔”声,像锈住的锁簧被终于拧动。血液重新流向苍白僵直的指尖,带来一阵细微的、酥麻的刺痛。掌心舒展开来,那三个模糊的、深嵌的月牙形旧痕,第一次毫无遮蔽地暴露在空气里,暴露在六月白晃晃的天光下。它们不再是耻辱或仇恨的徽记,它们只是伤痕,是记忆路过身体时,留下的、可以被凝视的地址。
拳头松开,变成了一只可以擦拭、可以握笔、也可以轻轻握住母亲那双被清洁剂浸泡得发皱的手的——普通的手。
他转过身,没有惊动母亲,轻轻走下楼梯。走出大楼时,炽热的阳光再次将他包裹。蝉鸣依旧,铺天盖地。但他不再觉得那声音是在锯开什么。那只是声音,是夏天本身沉重而澎湃的脉搏。他抬起头,眯着眼,看向太阳,看向太阳下这个喧嚷的、坚硬的、却依然有细碎暖意流转的人间。
他知道,有些东西永远失去了,像父亲坠落的那个下午。有些东西必须去面对,像母亲佝偻的背影。但此刻,他放下了拳头,不是为了原谅,而是为了腾出这双手。
去承担,去建设,去触摸。
去真正地生活。

1.《六月蝉鸣中,他放下了握紧三年的拳头》旨在传递更多网络信息知识,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与本网站无关,侵删请联系站长。
2.《六月蝉鸣中,他放下了握紧三年的拳头》中推荐相关影视观看网站未验证是否正常,请有问题请联系站长更新播放源网站。跳转第三方网站播放时请注意保护个人隐私,防止虚假广告。
3.文章转载时请保留本站内容来源地址:https://www.chinaarg.cn/article/ad444cf485a3.html